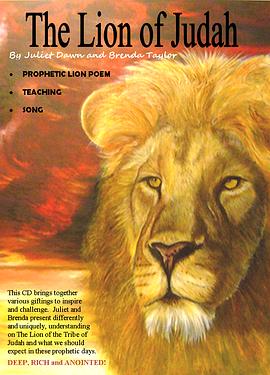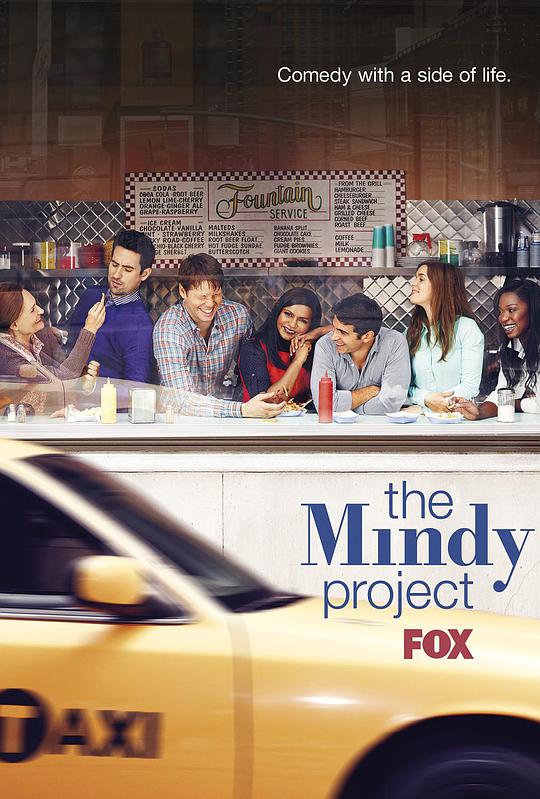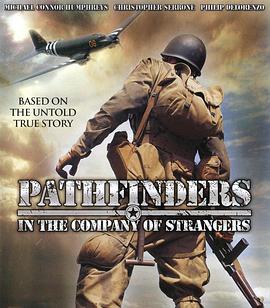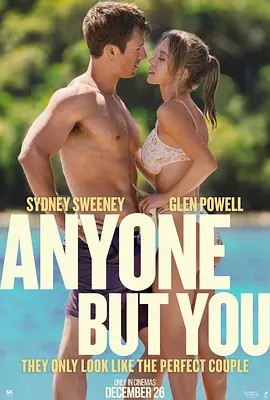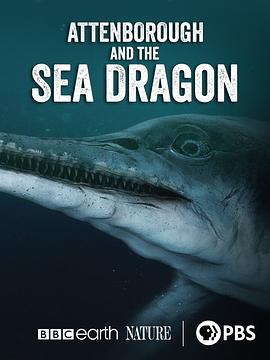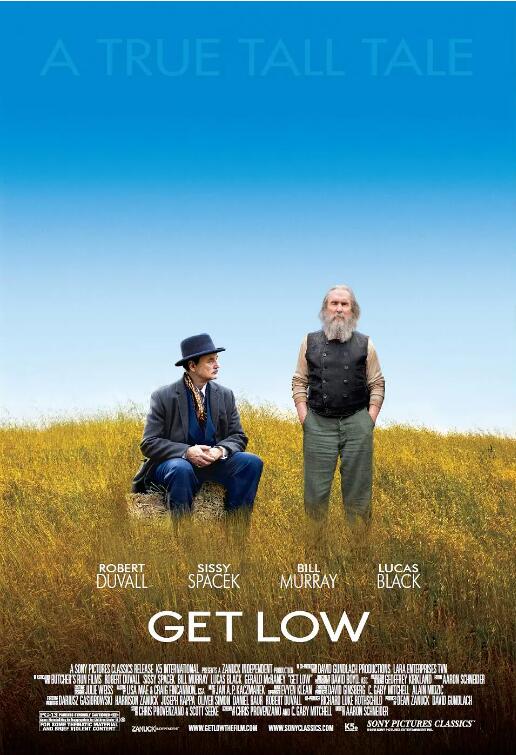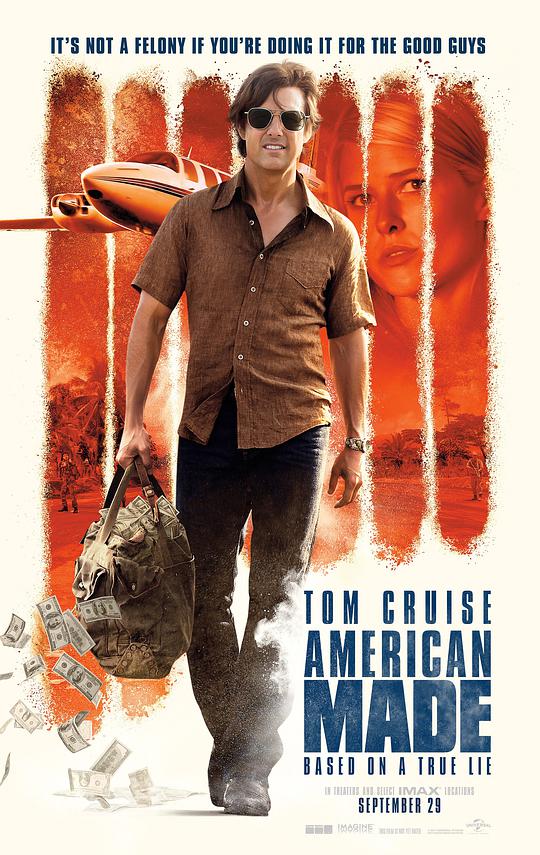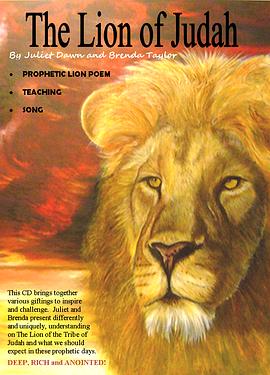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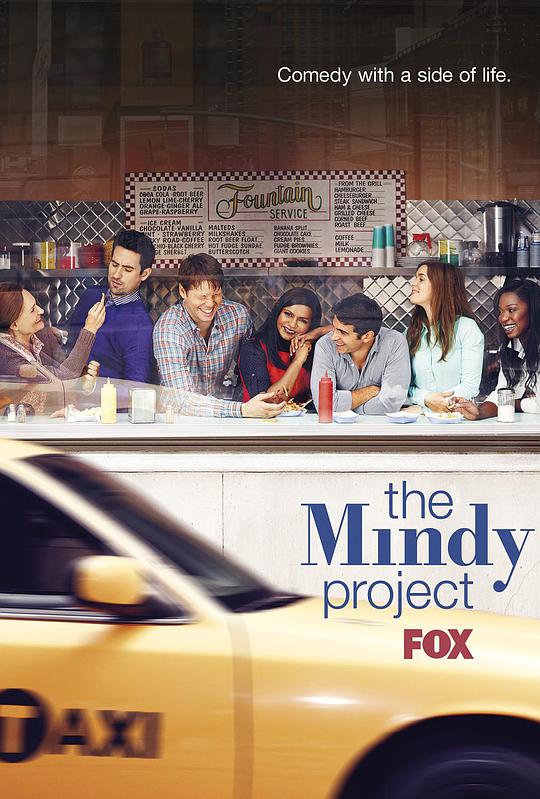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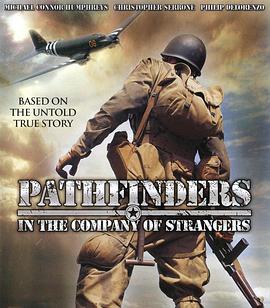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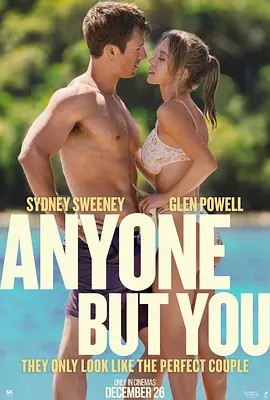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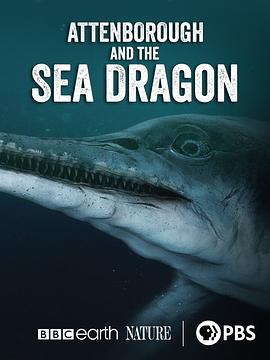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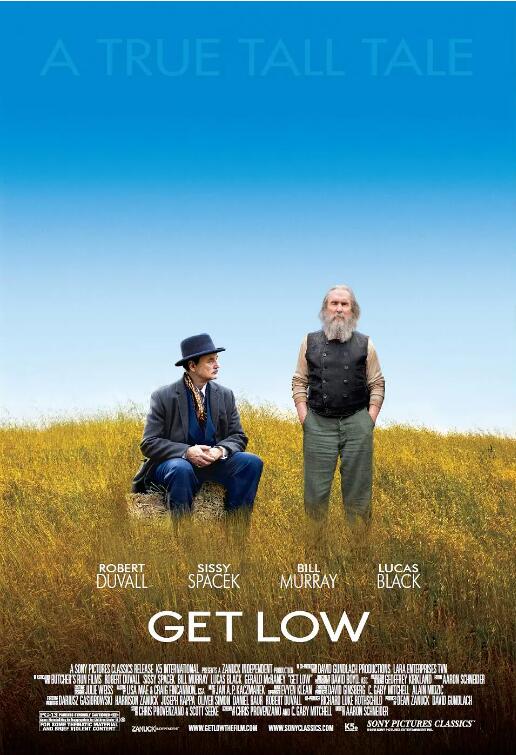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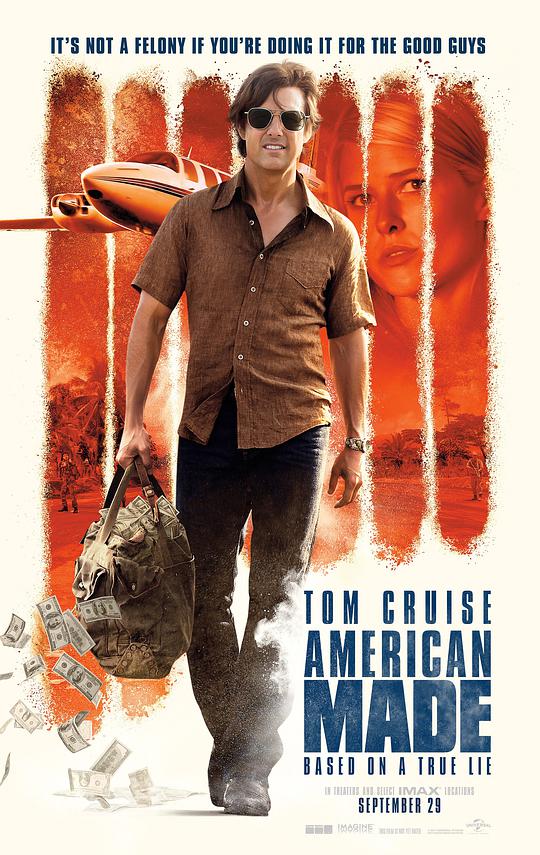








这个世界出BUG了
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两年前,我在北京打一个六座车,一上车,声音就让我感觉很熟悉,透过后视镜,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我人生的第一套高尔夫球杆,就是他送的。他曾经是北京最大的茶叶供应链的老板之一,在三里屯有很多大平层。我打开滴滴一看,果然姓氏也对得上,下车之后,找朋友打听了一下,才知道,这位大哥,几年前破产了。
在车上,他大概率也认出了我,我们并没有相认,这也许就是成年人的一种默契。我一直想做一个关于滴滴司机群体中曾经富豪的故事,于是选题安排下去了,成稿,等了两年。
1990年,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,一个全新的时代正迎面走来。
老徐,本期故事的主角,那年17岁,他从老家浙江随着父亲来到上海,随着父亲从票贩子到五金厂,家里的生意越滚越大,短短几年,自己和弟弟就成了别人嘴里的“富二代”。
往后20年里,他的人生按部就班:父亲提供启动资金、自己开厂、赚到第一桶金、生意越做越大,成为年入千万的老板。他至今忘不了在90年代开上桑塔纳时,村里人的羡慕和惊叹。
但是如今的他,在2025年,依旧还在开车,只是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如今的他,每天将近12个小时都待在车上,滴滴成了他的老板,而他自己则从“徐老板”到“徐师傅”,车换了,路变了,他的故事,也换了种方式,重新开场。
回首半生,老徐少年时就开始做生意,没怎么读过书,虽然认知和眼界都不足,但靠着时代红利和家人托举,也能风光一阵。他一度觉得自己就是天选的主角,等独自面对风浪时才发现,曾经熟悉的江湖手段不再管用,数千万的债务,瞬间淹没了曾经的风光。
而在滴滴平台,像老徐一样的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板们,其实很多很多。
他们是时代的缩影,也是时代的必然。
90年代的600万是什么概念
“哥,我们发了!”在老徐租来的吉利帝豪里,他一边开车,一边向我描述记忆里最难忘的场景,那是自己第一次获得人生巨款。
90年代末,上海到处都在建楼,修路。老徐和弟弟的厂房赶上村里修路拆迁,光自己就分到了600万,说起数字的时候,他眉飞色舞,眼里有光。
“当时什么感觉,你懂吗?就像刚睡醒,懵着头往前走,‘砰”的一下,撞上了一座山,还是金子做的!”
“五金工匠走四方,府府县县不离康”,如今的浙江永康,有“世界五金之都”的名号。在90年代,这里造的保温杯、防盗门、滑板车、电动车流向全国。永康人甚至在家就能开小作坊——几台冲床、几个亲戚,就能生产门锁、合页、水龙头这些日用五金。
老徐的父亲,一个早年来上海闯荡的永康人,已经靠做五金厂站稳了脚跟。看到父亲的成功,兄弟俩觉得这生意他们也能做。
“我们哥俩刚到上海的时候,也摆小摊卖点蔬菜水果,到千禧年前,攒了小几万了,我说‘兄弟,咱俩也去搞块地,造厂房,老爸能成,我们肯定也行。’”
1995年,兄弟创业,父亲除了给30万的启动资金,后面再也没管过他俩。“我爸那会儿生意忙得很,有时候三四个月才见得到一回,只能自己摸黑干了。”
老徐告诉我,自己兄弟俩都是心高气傲的人,父亲不管不顾,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好胜心。然而真开始做了,才发现没那么容易。建厂以后,订单时有时无。头两年,账面上一直是亏的,全靠父亲那点启动资金撑着。
这时候,弟弟的作用就显出来了。“我弟长得帅,嘴也甜,在村里很招人喜欢。那会儿流行认干妈,村主任喜欢他,就把他认了回去。”这层关系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,特别管用。
老徐记得,他们去办建厂手续时,别人跑三五趟,他们一两趟就盖齐了章。弟弟很懂人情,逢年过节总提醒他:“哥,该去看看干妈了,还有书记他们。”于是,几条好烟,几瓶好酒,就被送进村干部家里。
“东西不贵,就是个心意。”老徐说,“效果很好,后来我们厂的水电费,都没人催着交了。”
命运的彩蛋,在他们开厂的第三年,随着浦东开发的推土机一同到来。90年代,浦东大开发,很多地方要拆迁。老徐和弟弟办厂的那块地,正好被规划了进去。
因为有干妈的提醒,他们提前给厂房办好了手续。拆迁队来的时候,弟弟的厂先谈妥,接着过了几个月轮到了他。
那是1999年,在人生最好的25岁,老徐拥有了六百万现金,像一场不真实的梦。“当时20万就能在上海静安买套80平的房,我能买上30套!”他的语气里,有兴奋,有遗憾,有还没消散的激情。
钱到账那天,兄弟俩的路也分开走了。
弟弟选择留在上海。做起了本地的果蔬供应链,得益于那几年在政商界攀附上的干妈、干爸、干姐妹,生意越做越大,浦东大部分学校的食堂,甚至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的配送,都被他弟弟揽在了手里。
而老徐,在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时,带着这笔钱,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——浙江丽水。
在上海,他是“徐家的儿子”,是“徐老板的哥哥”。但揣着六百万回到镇上,在乡亲们眼里,他成了真正有本事、见过大世面的“大老板”。
他开始投资,开了一家服装厂,又建了养鸭场。每个摊子都铺得很大,他觉得自己踩准了每一步,却不知道,潮水已经开始转向了。
2014年负债几千万是什么概念
在浙江丽水的缙云县,当地最出名的除了烧饼,还有麻鸭。
缙云麻鸭个头不大,毛色灰褐带麻点,长得很像麻雀,它肉质紧实,能生出少见的青壳蛋,在市场很受欢迎,在老徐记忆里,爷爷那辈的父老乡亲就开始靠养麻鸭赚钱了。
他回去的第一件事,是承包了一块地,继承了爷爷那会儿就在做的养鸭生意。
在20多年前,缙云那边虽然有不少人养鸭子,但还没有规模化和工厂化,散户有很多。老徐就钻了其中的空子,“我弄个养殖厂,孵化鸭苗,免费分给散户养,钱从哪赚呢?饲料,他们必须从我这儿买。”
这种“绑着卖”的模式,在陆续干了几年后,他开始尝到了甜头。
生意最火的时候,他每天一睁眼,账户里就能多出三十多万的纯利。他形容那感觉:“仿佛以后都能赚这么多,人都飘着,觉得这路子走对了,规模还能再大。”
膨胀以后,他找银行贷了款,把原先的厂房扩建到足足16000多平,每次要还的贷款数额不小,可那几年行情实在好,每天哗哗进账,覆盖掉还款绰绰有余。老徐算过,再过几年就能结清,往后就是净赚。
命运的齿轮在2013年悄然卡住。那一年,弟弟在上海,兴奋地打来电话,告诉他自贸区成立了,眼前都是新机会,问他要不要一起投点什么。
彼时老徐的心思全扑在养鸭上——上半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禽流感,当地政府要求他暂时停业。
“我弟真是命好,他在风口,我在风头”,他开玩笑地说道。那会儿他还在等开工通知,“天灾嘛,总有过去的时候”。虽然没有心思参与弟弟的大事,但他还是打了不少钱过去。
真正的闷棍在2014年打了下来。年初的时候,他收到了责令整改,说他这厂子“手续不全”,属于违建,要拆。
老徐当时就蒙了。“扩建那会儿,跟村里镇上都说好了的,备个案就行,没想到规矩全变了。”他忽然意识到,这里不是上海,哪怕是在老家,身边也没有能提前递句话的“干妈”了。
拆厂房那天,他站得老远看着。“当时我脑子空了,不知道该干什么,前几年赚的钱都搭了进去,本以为能做大的。”他叹了一口气。
十年前,拆迁给他带来了人生第一桶金,十年后,还是熟悉的推土机,让他债台高筑。
厂没了,生意断了线,但银行的贷款账单,每个月都准时寄来,“到底欠了多少,我没敢仔细算,一笔糊涂账。”老徐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几千万总是有的。”
为了还债,他能卖的都卖了。“0几年流行炒房,嘉兴有个尚东名邸,我和弟弟都是按层买的,后来他高位套现,我想留着收租。”
结果他破产了,这些房子被法院一套接一套拍卖,为了捞他这个大哥,弟弟也卖掉了好几套房。退休多年的父母,几乎掏空了储蓄,“我妈现在天天在老家种地呢,没办法了。”
“我把一家子都拖下水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睛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车尾灯。
开网约车也一样有坑要踩
老徐彻底把债还清,是前两年的事。中间那段日子,是他人生里最黑的一段。
厂子倒后,他什么活都干,最多一天打4份工。当过小区保安,给人送过外卖,天不亮就爬起来送牛奶。“工资刚打进卡,立马就被银行划走扣债了,那会儿全靠老婆工资撑着。”
老徐真的想过要跳楼,但转念一想,两个女儿都在上学,只能咬着牙熬下去。“之前一起投资农家乐的老板听说了我的情况,打电话跟我说:‘老徐啊,要不你来帮我看厂,一个月给你开1万。”
尽管在最难的时候,他甚至跟女儿的老师借过钱,但他还是拒绝了朋友的提议。“太丢人了。”李嘉诚说过一句话,大概意思是,人阔的时候,脸面就是张纸,穷的时候才知道,它捅不穿。
去年,大女儿在杭州成了家,小女儿也来杭州读大学。他不放心,跟着过来了。试过几样零工后,他开起了滴滴。
老徐来之前研究过,杭州雨多,交通管制很严,送外卖成了技术活,还不安全;开网约车没啥门槛,关键是不看征信,对他这种背过债的人来说,是扇难得的门。
门是进了,坑却也等着。 他所有的车早已变卖抵债,只能租车。刚开始,他在BOSS上看到不少宣传“0押金、不租不买”的网约车公司,听起来很划算。就选了一家,等签完合同,才发觉掉进了连环套。
首先是“0押金”骗局,他说这跟高价租车没区别。“合同里会要求你跑8500的流水,达标就给你发4500的工资,那不就相当于一个月交4000的租金吗?但公司给的车,去市场租可不贵,基本都是3000左右。”
其次是反悔难。老徐察觉自己被坑后想退出,发现人事当初说好的“提前一个月告知就行”不作数了,按合同规定,想退出得跑满当月8500的流水,而且这指的是平台给公司的结算额,司机实际要跑到近一万才行。
“你知道一个月跑一万的流水有多难吗,还得跑公司指定的平台,每天出车要到14个小时,你就去跑吧。”
最后是信用套牢。老徐后来才弄明白其中的门道:“那些渠道公司,他们是拿我的支付宝去租车,而且是先用后付,等于自己没成本,让我替他们打工。”就算他扔下车不要了,每个月的租车费还是从他支付宝上扣。
老徐庆幸自己只签了半年的合同,但提到退车时的场景,还是感觉荒谬,“熬到最后一个月,以为总算解脱了。去退车,人家说有个15天的车辆闲置费,150块钱一天。”最后算下来,他那个月等于白干。
每一个滴滴富豪都想东山再起
吃了亏,也长了记性。 后来他换了家正规公司,每月租金三千。他给自己定了规矩:早上五点半出车,冲早高峰;跑到四百块流水,就收工回家。
“我搞了个慢充桩,一个月电费只要两百多块。烟酒槟榔全戒了,从家里带饭。一天吃两顿。”精打细算下来,老徐每月差不多跑二十七天,能净挣九千到一万。
他说,司机和平台都有“三个月蜜月期”。“刚开始跑滴滴多一点,对新人友好,那儿的单子又好又多,勤快点时薪能到四十块,而且提现比其他平台快,‘+1’日到账。”但是等上道以后,自己也开始变得“老油条”。
他下了各种接单平台,研究政策规则,平台派单的逻辑和免佣时段政策,不是什么单子都接了。
“现在我最喜欢跑高德,滴滴太便宜,跑得少了。”老徐说。如今网约车平台几十家,卷得厉害,司机的选择也多了。“以前被扣了服务分,还紧张得不行,拼命想补回来。现在无所谓了,这家不行就跑那家,反正赚得都差不多。”
刚开始跑车时,他只开了滴滴作为主平台,偶尔接点T3出行、曹操等平台的派单,但半年后,“车里放四台手机,多的时候开十多个平台,高兴跑谁就跑谁。”
老徐告诉我,只有乘客上了车,网约车司机才知道是哪个平台派单,但自己绝对不接花小猪。“有时候接到了,我就直接让乘客下车,这单不做了。”他解释,不是对乘客有意见,是平台给司机的价,实在太低,跑一趟亏一趟。
这种“挑单”,在他们圈子里很常见,只针对个别“吸血”太狠的平台。
如今,已经被人叫了一年的“徐师傅”,他也逐渐上道了,但老徐仍然只把眼下当作“过渡的手段。”他计划着,等征信养好了,再去银行贷款,重新创业。
他最近常刷外贸相关的短视频,“过几年,去非洲,或者去那个巴基还是巴勒斯坦的,不是都说中巴友谊吗,那里机会多,我打算去试试。”
老徐爱看周润发的《英雄本色》,小马哥叼着火柴、用钞票点烟的那份不羁,在1986年点燃了无数街头少年的梦。
电影里,小马哥瘸着腿,对豪哥说:“我要争一口气,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,我是要告诉人家,我失去的东西,我一定要拿回来!”
那时老徐13岁,在录像厅昏暗的光线里,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该活成的样子。